知所進退陳平原

陳平原,1954年1月生於潮州。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,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、七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。198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,獲文學學士學位﹔1984年畢業於中山大學,獲文學碩士學位﹔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,獲文學博士學位。同年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、副教授(1990年起)、教授(1992年起),2008—2012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。主要研究領域有20世紀中國文學、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、中國小說史、中國散文史等。
◎《南方》雜志記者�劉艷輝 發自北京、廣州、潮州
◎本文責編�李焱鑫
2021年9月,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多了一個新職務—暨南大學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。
他跳出潮州看潮州,強調研究要超越地域,超越文史學科思維,超越學院與社會的邊界,同時“拾遺補缺”,真正連接好研究、社會與企業,更好推動潮州文化的傳承與創新。
從成立儀式,到研討會、懇談會,甚至“潮人潮學”公眾號文章審核,陳平原身體力行。對熟悉他的廣東人來說,這並不意外。
在這位大學者身上,“潮州人”一直是張顯眼標簽,雖然多年在外,但他始終心系家鄉的教育及文化建設。近年來,他出任潮州市文化顧問以及韓山師范學院董事,策劃“韓江講堂”,和林倫倫、黃挺合作主編《潮汕文化讀本》,一舉一動備受關注,頗受贊譽。又與深圳多有合作,比如出任南山區文化顧問和南山圖書館理事,粗略統計,12年間共參加學術文化活動20場。
他不需要,也從不借機自我標榜。面對媒體和公眾,他再三聲明,無論潮學、嶺南文化還是人文灣區建設,都不是他的專業領域,敲鑼打鼓可以,粉墨登場則不敢。
他自帶流量,卻拒絕迎風起舞,在關注現實與迎合公眾之間選擇前者,在採訪問答的方寸之間審慎把握:“從媒體角度,話題越熱鬧越好﹔作為學者,我必須知所進退。”
陳平原曾形象地自喻為“壓艙石”,對熱鬧、時尚保持警惕,矢志不渝地追求著學術與人生合一。30余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,他以“我手寫我心”,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學問底下的溫情、詩意與想象力,追尋文字、聲音、圖像背后的真實歷史文化景觀,不厭其煩地詮釋著何為“有情懷的學術”以及“學者情懷”。
有境界自成高格。陳平原的學術志向與野心,通過一件往事可見一斑。1999年,北京大學“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”成立時,陳平原揮筆道,該中心的宗旨還有一條:研究艱難中崛起的20世紀中國,希望在重鑄民族魂以及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和文化建設方面,發揮更大的作用。
作為大學教授,他不忘育人本色,在文學史、學術史研究中更多從教育體制入手,可謂用心良苦。在他看來,所有思想轉變、文學革命、制度創新等都必須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,且根深蒂固、不可動搖。
對陳平原的採訪,本文既不是第一篇,也不是最后一篇。目前已有七八十篇採訪問答,被細細整理錄入《京西答客問》《閱讀·大學·中文系》等書中。本文隻能算是滄海一粟,謹供讀者進一步了解陳平原的所思所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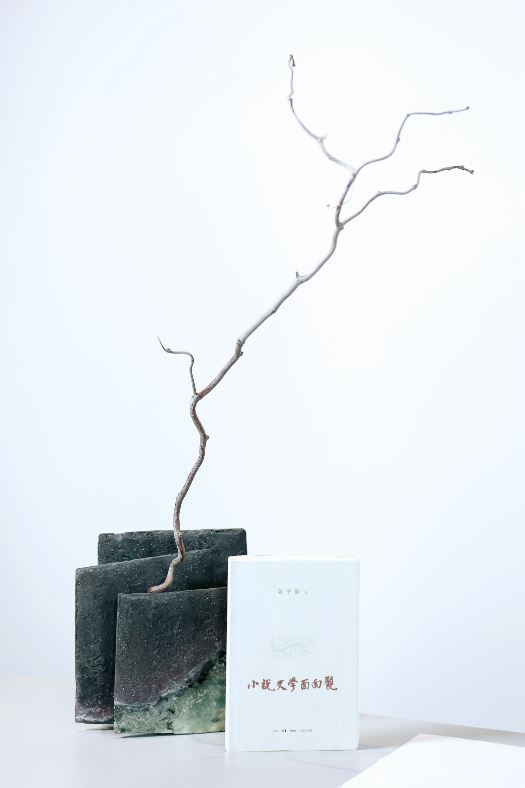
對特殊時代、特殊課堂的紀念
“從書裡談到書外,長長短短、瑣瑣碎碎,如此扶老攜幼,能使研究對象更加血肉豐滿。”
《南方》雜志:祝賀您的新書《小說史學面面觀》出版。您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從事小說史研究,中間轉向學術史、教育史。能否介紹下本書寫作緣起?
陳平原:刊行於1988年的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,是我的博士論文,獲得很多學術榮譽,最得意的是出版30年后,獲第四屆思勉原創獎。我在小說史研究方面的著作,還有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》《千古文人俠客夢》《中國散文小說史》等。但這回的《小說史學面面觀》不一樣,屬於“學術史”而不是“文學史”,那就是“中間轉向了學術史、教育史”一圈的結果。在此書最后一章,我審視自己的小說史研究,辨析其中的功過得失,希望給后來者提供借鑒。
至於寫作緣起,最初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,北大改為線上教學。對著空蕩蕩的鏡頭宣講,不再與學生面對面,無法交換眼神,不僅不精彩,而且容易忘詞。為了備忘,我寫下了部分講稿或詳細的大綱。課后意猶未盡,干脆整理成文,交給《文藝爭鳴》刊發,也算是對這一特殊時代、特殊課堂的紀念。
《南方》雜志:該書的研究對象不僅有魯迅、胡適等這些讀者都比較熟悉的中國學者,還有普實克、夏志清、韓南等外國學者。這樣的選擇有何考慮?
陳平原:這就說到我希望做到的“面面觀”,包含以下三個層次:第一,描述並評價不同時代、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於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思路及著述,目的是呈現不同的學術視野與方法。第二,選擇這12位學者,不一定業績最佳,但都別具特色,很能引發思考與討論。換句話說,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,試圖凸顯的是研究者的立場、趣味及方法。基於此設想,本書舍棄了很多主要貢獻不在小說史學的優秀學者,即便在小說研究領域,也不追求面面俱到,而是採取“舉例說明”的方式,選擇我較為熟悉且感興趣的話題,反復敲打,希望能得出若干獨特的發現。第三,我自己的解說與論述同樣不拘一格,有時長篇大論,有時點到為止,就像課堂講授一樣,“大珠小珠落玉盤”的同時,還得保持一定的水分與空氣。如果兩個小時全是實打實的干貨,會讓人聽不下去的,必須張弛有度,靈活多樣,且講究韻律與節奏,方能維持聽眾的注意力。
《南方》雜志:“既學問,也人情,還文章”,是您對這本書的理想設計,也代表了您的著述風格。形成這樣的風格經歷了哪些過程?
陳平原:關於這本書採用何種文體,到底是論文還是隨筆,我一開始很猶豫。最后選擇了這麼一種介於專門著作與課堂講義之間的寫作形式。有理論闡釋、史料鉤沉,但也穿插閑話,兼及師友逸聞。從書裡談到書外,長長短短、瑣瑣碎碎,如此扶老攜幼,能使研究對象更加血肉豐滿。也正因此,此書比我以往出版的諸多專業著述要好讀很多。當然,這與我內心深處對過於學究氣的學術論著不太滿意有關。到目前為止,這個試驗的結果還可以,在專業雜志上發表,朋友們大都認為有見地,不怎麼八股,算是別具一格吧。但這是論題本身以及生產過程決定的,不能硬套到我此前此后的所有著述。
文學教授的別有幽懷
“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,呼喚那些壓在疊床架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、詩意與想象力,在我看來,既是歷史研究,也是現實訴求。”
《南方》雜志:無論是研究文學史,還是學術史,您都不把它單純作為一種知識體系,而是更多地從教育入手,有哪些用意?
陳平原:我曾經說過:“從事學術史、思想史、文學史的朋友,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。因為,百年中國,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,乃值得大書特書的‘關鍵時刻’。而大學制度的建立,包括其蘊含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,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,更是帶根本性的—相對於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移而言。”反過來,教育史的思考與撰述,對我從事文學史或學術史的研究,大有裨益。這一番“游歷”,在我已出版的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》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以及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》中,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比如,談論作為知識生產的“文學史”,必須體會其中體制與權力的合謀,意識形態與技術能力的縫隙,還有個體學者與時代氛圍的關系﹔眾多努力中,從“教育”角度切入,可以兼及學問體系、學術潮流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,我以為是比較穩妥且可行的。
《南方》雜志:就當下而言,落實文學教育關鍵在哪裡?
陳平原:進入現代社會,“合理化”與“專業性”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﹔“文學”作為一個“學科”,逐漸被建設成為獨立自足的專業領域。最直接的表現便是,文學教育的重心,由技能訓練的“詞章之學”,轉為知識積累的“文學史”。如此轉折,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,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。我在《文學如何教育》一書中描述了文學教育的十個方面,以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“大學五書”及“學術史三部曲”為根基,力圖將學院的知識考辨與社會的文化批評相勾連,在教育制度、人文養成、文學批評、學術思想的交匯處,確立“文學教育”的宗旨、功能及發展方向。相對於學界其他同仁,我談論文學史及文學批評,更多從教育體制入手,這也算是別有幽懷。作為一名文學教授,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,呼喚那些壓在疊床架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、詩意與想象力,在我看來,既是歷史研究,也是現實訴求。
建立自己表達的立場、方式與邊界
“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學養及思考,乃是現代中國學者亟須錘煉的基本功。”
《南方》雜志:去年出版的《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》,是您的“學術史三部曲”收官之作。什麼是“述學文體”,這一研究有哪些重要意義?
陳平原:一般認為,治學的得失成敗,關鍵在政治立場、文化趣味、專業知識以及時代風潮﹔至於“述學文體”,似乎無關緊要。可在我看來,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學養及思考,乃是現代中國學者亟須錘煉的基本功。這裡談的不是一般的寫作技巧,而是中國學者如何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,建立自己表達的立場、方式與邊界。這涉及整個現代學術生產機制,比如,什麼才叫論文,為何需要專著,教科書意義何在,演說能否成為文章,引文的功能及邊界,“報章之文”與“學者之文”如何協調,能否“面對公眾”而又不失“專業水准”等,這一系列難題背后,牽涉到整個教育體制以及知識生產方式。如再說開去,則是全球化視野、西學東漸大潮、話語權爭奪等在現代中國學界的自然投射。而這些,並不是一兩句“學術獨立”或“博學深思”就能解決的。
《南方》雜志:您的研究不限於文本,同時關注了“城市”“圖像晚清”以及“有聲的中國”,透過不同的媒介發現了不同的文化景觀。為什麼從這些角度入手?
陳平原:10年前,我發表《“現代中國研究”的四重視野—大學·都市·圖像·聲音》,談我為何要在主營的文學史與學術史之外,如此拓展學術疆域與視野。某種程度上,這既是自我期待,更是學術展望。關於“大學”與“圖像”,我的成績還可以,在北大出版社刊行“大學五書”,除《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》,我還在東方出版社推出了《圖像晚清—〈點石齋畫報〉》《圖像晚清—〈點石齋畫報〉之外》。“有聲的中國”很有潛力,已發表了若干文章,只是尚未正式成書。有點遺憾的是都市研究,我起步很早,但效果不太理想,去年出版的《記憶北京》與《想象都市》,顯得有點散亂。之所以撒得這麼開,除了學術野心,更重要的是為我的學生探路。放長視線,若他們在學術上有大的推進,那我的“提倡有心,創作無力”也就值得了。
對時尚保持必要的警惕
“我看過很多聰明人,之所以摔跟頭,就因為過分看重時尚,什麼熱就做什麼,且老想抄捷徑,最后的結果是欲速則不達。”
《南方》雜志:投身學術40年來,您共寫下30多本著作,可謂著作等身,並獲得很多學術獎勵。最近四五年間又出版了七八本新作。您是如何做到的?
陳平原:人文及社科沒有國家獎,最高的也就是教育部頒發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,我獲得了五次(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屆),其中兩次還是一等獎。不過,60歲以后我就主動放棄了,不再申請此獎項。因我發現,現在申請名額下放到學校和院系,你再參與,就會擠佔年輕教師的發展空間。如果是校外評審,不用填表自吹自擂,那樣的獲獎,我很開心,比如第四屆王瑤學術獎著作獎(2016)、第四屆思勉原創獎(2017)、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(2019)、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(2021)等。至於最近幾年出書多,那是因為我同時做好幾個題目,經過長期積累,剛好這個時候出來,像獲得文津圖書獎的《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—晚清畫報研究》,以及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的《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》,都是經營了差不多20年。
《南方》雜志: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治學方法和寫作習慣,以及下一步研究重心?
陳平原:我是1977級大學生,曾下鄉插隊8年,學問上起步很晚。上大學后,走得比較順暢,算是勤能補拙吧。說到研究方法,沒有一定之規,跟時代背景、學術領域以及個人性情相關,關鍵在於學會自我反省,盡可能少走彎路。另外就是對時尚保持必要的警惕—不管誘惑多大,倘若不是你想要或你能要的,就應該不為所動。我看過很多聰明人,之所以摔跟頭,就因為過分看重時尚,什麼熱就做什麼,且老想抄捷徑,最后的結果是欲速則不達。隻要不太笨,以中人之資,肯下苦功,持之以恆,總能做出成績來。至於寫作習慣,那就更是因人而異了。相對於其他專業,學人文的,擅長寫文章,這點很要緊。我注意到文人學者中,凡到老年還能產出好文章的,十有八九是養成經常寫作的習慣,類似“曲不離口,拳不離手”。今天因為嚴苛的學術考核,導致某些年輕學者寫得太多、太水,這是另一個問題。我想談的是很多教授成名后,過早地喪失學術創造力,再也寫不出好文章來。
我的習慣是,每年用心經營三四篇像樣的大論文,另外還得有八九篇別的文章,包括一般論文、文化評論或學術隨筆。我當然知道,一個學者真正有創見、能流傳得下去的好文章,不會很多的﹔你不能保証寫下來的,就能傳得下去。不懈思考,經常動筆,長長短短,好好壞壞,除了多少有所收獲,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學術敏感、思維能力、寫作激情以及文字管控能力。至於下一步研究重心,就不在這裡啰嗦了,用我們家鄉話說,“撿有豬屎呾有話”(比喻事情做好了就有話講了),在此之前不要吹牛。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